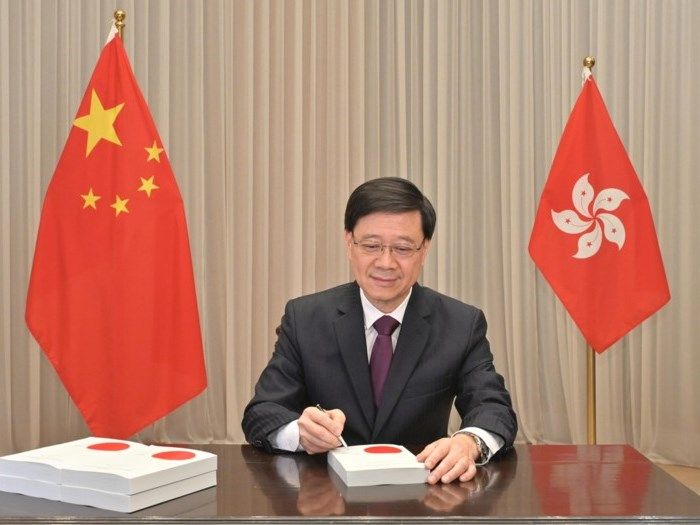| 【 第1頁 第2頁 】 | |
| “一國兩制”白皮書十周年:央港權力關係回顧與前瞻 | |
http://www.CRNTT.com 2024-06-26 11:31:14 |
【摘要】學界關於全面管治權的兩種概念界定方式是不同階段下全面管治權的權力內容變動的體現。全面管治權授權產生高度自治權,這種授權關係是單向度、分層次、有期限的;中央作出授權以後,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關係包括直接管治的關係和監督關係。在管治關係中,中央的管治權力與高度自治權不是截然二分的,但是必要時中央行使共同事權具有優先性。中央監督特區行使高度自治權意味著不直接處理特區自治範圍內事務,但監督的對象應及於高度自治權的全部領域。全面管治權及其相關表述的提出實現了“一國兩制”框架內央港權力的平衡,並為央港良性的權力互動關係指明了一個可操作的方向。 一、問題的提出 “全面管治權”的概念落地已經滿10年,其官方表述主要經歷了三次代表性的演進:第一次是2014年6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印發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下文簡稱《“一國兩制”的實踐》白皮書),首次規定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下文簡稱中央的直接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區政府依法實行高度自治權。對於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第二次是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首提把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也正是因為十九大報告提出“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的主張,全面管治權的相關研究在此之後迎來了一次激增。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一國兩制”的實踐》白皮書新創“全面管治權”的概念以前,官方文件的表述是把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因而在這類文本語境中,全面管治權與中央的權力可以作同義替換,全面管治權就是指中央權力。在此基礎上,國新辦又於2021年12月發佈了《“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進一步將全面管治權的具體內涵表述得更為精當、明瞭,即全面管治權包括三個部分,分別是中央的直接權力、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以及中央對特區高度自治權的監督權。這表明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之間既存在授權關係,又存在監督關係。監督是授權的必然結果,監督的對象即授權的內容。第三次是2022年7月1日,習總書記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講話中進一步提出,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是統一銜接的。既然在“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的說法中,全面管治權就是指中央權力,推而及之,“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統一銜接”表述中的全面管治權也是指的中央權力。 官方文件中全面管治權的不同表述形式在某種程度上促使內地學界對什麼是全面管治權的問題產生了差異化的觀點,並大體形成了全面管治權的兩種概念界定方式:其一,全面管治權是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下中央對包括香港特區在內的所有地方的所有事務進行管轄和治理的權力。其二,全面管治權是指中央的權力,相當於憲法、基本法規定的中央在香港行使的主權權力。“同一概念,不同界定”是不同階段下全面管治權的權力內容變動的體現。全面管治權授權產生高度自治權,在作出授權以前,全面管治權包括對特區的所有地方的所有事務進行管轄、治理的權力;作出授權以後,全面管治權表現為中央行使的主權權力。本文試從規範論視角分析不同階段下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複雜關係,並且將兩種權力的關係問題進一步細分為以下兩個子問題,分別加以回應:其一,作為整體的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是什麼?其二,全面管治權各組成部分與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是怎樣的?回應這些問題的同時,本文將進一步探究全面管治權的內容和邊界,特區行使高度自治權的紅線、底線,從而試圖為實踐中處理兩種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提供某些操作性指引。 二、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關係 全面管治權本質上是一國的治權,但是比治權概念多了一個修飾語——“全面”。“全面”二字與高度自治權中的“高度”二字對應,是指向權力集合體的特有屬性,作為法律用語是一個模糊的形容詞。相比於“管治權”,修飾語“全面”一詞實則更需要解釋。全面的管治權意指特區的全部治權在中央,中央有權對香港的所有地方、所有事務進行管轄和治理,這是“全面”一詞內容的合理延伸。中央擁有原初的管治特區的全部權力,因而高度自治權的全部內容源於中央的授權。 全面管治權授權產生高度自治權,在作出授權以前,作為整體的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是授權關係。授權的本質是權力行使的轉移,而非權力所有的轉移。藉由授權行為,特區獲得了這部分權力的行使權,但權力的所有權屬於中央。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中央”一詞限定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家主席、國務院、中央軍委,而不是這些機關的附屬機關,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設立的機構在內。倘若離開這一主體範圍設定,文章得出的多數結論恐怕難以經得起推敲。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授權關係在符合授權的一般原則的同時,又因為滿足了單一制國家對特殊地方的治理需要而表現出特殊性。在筆者看來,這種特殊的授權關係至少可以作以下幾個層面的解讀: 授權是單向度的。單向度的權力授受關係始終遵循地方的權力源於中央授予的邏輯,表明:其一,中央授予特區多少權力,特區就有多少權力;其二,授權不是一次性作出的,中央可以適時擴大、變更授權範圍,但這都是授權者的單方處置行為,特區不應自設權力;其三,基本法未列明的權力屬於中央。基本法起草之初,就有人主張基本法存在未列明的部分,該部分既屬於中央事權,又與特區存在關係,即所謂的“灰色地帶”。起草委員會採納了這一意見,將其概括為“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寫進基本法(主要見《基本法》第二章,其他各章均有涉及),由中央負責行使相關權力。①此外,根據《基本法》第20條,香港特區可享有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授予的其他權力,特區從而可以被授予基本法未列明的權力,同樣說明基本法未列明的權力屬於中央。單向度的權力授受關係意味著中央與特區的監督關係也是單向度的,而不是互相監督的關係,特區也不享有拒絕接受監督的權力。 授權分層次。基本法被視為授權法主要是針對高度自治權而言的。值得注意的是,通過基本法,中央國家機關同樣也獲得了憲法沒有具體規定的權力,比如國務院對行政長官、政府主要官員的任免權,國務院發出指令的權力,全國人大常委會增減附件三所列全國性法律的決定權等等,不一而足。故基本法作為授權法實際包括了中央橫向層面的,以及中央和地方縱向層面的授權。王禹教授從動態角度詮釋了這種分層授權的過程,他首次將憲法、基本法中的授權概念分為第一次授權、第二次授權。第一次授權是通過憲法、基本法等規範性文件賦予某一主體初始權力的授權。第二次授權建基於第一次授權之上,是有權機關再次將憲法、基本法賦予自己的權力授予其他機關行使的授權。②如果說第一次授權形成了中央的直接權力,並使特區初步獲得相比其他任何地方的權力更“高度”的自治權,那麼第二次授權又使特區獲得了相比第一次授權所形成的自治權更為“高度”的權力。對於特區而言,兩次授權效果疊加後形成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基於此,高度自治權中的具體權力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中央第一次授權以及第二次授權的權力。這種權力劃分方式的實踐意義在於,必要時中央可以行使第二次授予特區的權力。而區分高度自治權中的具體權力是第一次授權還是第二次授權的結果,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訴諸憲法的相關規定,判斷憲法是否已經將該項權力授予某個中央國家機關,並且該中央國家機關應僅限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家主席、國務院、中央軍委。 授權有期限。在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權力後仍保有必要的監督、變更授權乃至撤銷授權的權力。為防止中央恣意變更或者撤銷已經授予特區的權力,保證法秩序以及社會生活秩序的安定,基本法正文採取了兩種處理方式,一是規定五十年不變,二是規定了基本法修改的權力和程序並設定了內在限制。③其中,五十年是權力存續期的下限,五十年期限屆滿,中央有權收回已經授予特區的權力。中央可以收回,也可以不收回,如果不收回,則需適時修改基本法,對五十年進行展期。舉例而言,香港政府曾批地興建迪士尼樂園,並且將批出土地的期限定為一百年,雖然遠超基本法規定的五十年,但並不是越權行為,衹不過2047年7月1日以後,迪士尼能否繼續租用該土地存在不確定性。雖然在基本法正文中,高度自治權整體上受到五十年期限的保障,但其中具體權力受保障的方式存在部分差異,筆者將藉助程潔教授的權力劃分方法予以說明。程潔教授將基本法規定的中央對高度自治權的授權概括為三種方式,分別是一般性授權、具體授權和進一步授權的可能性,這是在基本法研究中區別於第一次授權、第二次授權的另一種常見的權力劃分方法。其中,一般性授權是特區可以根據基本法的規定直接行使的權力,無需中央作進一步授權。具體授權是指基本法原則規定特區可以行使某一方面的權力,同時規定特區在行使這些權力時還需中央具體授權。④由於基本法明確規定了一般性授權和具體授權的類型,這兩種授權方式大體受五十年期限的保障,衹不過後者還受到具體授權事項的進一步規限。進一步授權的可能性則集中體現於《基本法》第20條的規定。實踐中,全國人大常委會曾根據《基本法》第20條授權香港特區對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實施管轄。國務院在《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管轄的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範圍和土地使用期限的批復》中進一步明確,“土地使用期限自口岸啟用之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止”⑤,從而規定了2047年6月30日作為權力存續期的上限,與一般性授權、具體授權的存續時間相區別。 概言之,正因為授權有期限,而分權是長期的,沒有固定期限,因而高度自治權的形成源於授權而不是權力的讓渡或者轉移。其次,授權是單向度的,所有管治權力最初在中央,故中央授予特區多少權力,特區才有多少權力。在中央層面,全國人大擁有原初的全部權力〔見《憲法》第2條、第3條、第57條、第62條第(十六)項、《基本法》第2條〕,因而全國人大可以將權力通過憲法、基本法在中央的橫向層面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縱向層面進行授權,包括全國人大在內的中央國家機關再將部分權力轉授特區,從而與特區分享這部分管治權的行使權。 三、全面管治權各組成部分與高度自治權的關係 如前所述,籠統而言,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既包括授權關係,也包括監督關係。授權關係是作為整體的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關係,而監督關係則是全面管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監督權——與高度自治權的關係。主張將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或者統一銜接起來,就是在中央的具體權力與高度自治權的關係範疇內展開的。作出授權以後,中央監督特區行使高度自治權是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關係的常態,但不是二者關係的全部內容,即二者的關係既有中央直接管治的一面,也有中央監督的一面。 (一)管治關係 首先,中央的直接權力與特區高度自治權不是截然二分的,即某些權力僅特區行使,剩餘的、其他的權力由中央排他地行使,而是“某些權力中央可以行使,特區也可以行使”。⑥這種央港的共同事權並不是出於事權劃分體系的天然缺陷,而主要是分層授權下的獨特產物。上文已經介紹了憲法、基本法中第一次授權、第二次授權形成的分層授權結構。在這種分層授權結構中,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就是兩次授權效果疊加後的產物:通過第一次授權,特區獲得了對地方自治事務的排他性的權力;第二次授權又使特區獲得了部分中央管治權的行使權。對於中央第二次授予特區的權力,中央可以行使,特區也可以行使,但中央有最終決定權。舉例而言,《基本法》第158條規定基本法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同時,又授權特區法院對自治範圍內的條款進行解釋,以及對自治範圍外的條款進行有條件的解釋。第3款接著規定,如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為準。在劉港榕案、莊豐源案中,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就在判詞中承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是“全面而不受限的”(in general and unqualified terms),此項權力可在沒有訴訟的情況下行使。若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某條作出了解釋,無論是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還是第158條第2款,香港法院均須依循該解釋。⑦衹不過實踐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將解釋的範圍限制於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上,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專題小組曾在條文修改情況的報告中就此指出:“由於此項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涉及的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不作解釋”。⑧溯本求源,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源於《憲法》第67條第1款的規定,是第一次授權的結果。《基本法》第158條第2、第3款對香港法院基本法解釋權的規定,則是第二次授權的產物。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行使解釋權的效力自然要高於特區法院根據基本法所作解釋的效力。理論上,人大常委會可以重新解釋,從而對特區法院所作的錯誤的解釋進行否定,但在實踐中,中央行使基本法解釋權始終見步行步、異常謹慎,更不會輕易否定特區法院已經作出的解釋。迄今為止,人大常委會的五次釋法都是在特區法院對基本法相關條款存在分歧或者錯誤理解的背景下作出的。僅《基本法》第24條居留權條款經由行政長官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而被重新解釋外,法院對基本法所作的其他解釋均未被否定。⑨ |
|
【 第1頁 第2頁 】 |
相關新聞:
- 新時代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路徑策略 (2024-06-26 11:24:53)
- 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的中華文化認知基礎 (2024-01-31 14:48:40)
- 以弘揚黃帝文化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 (2024-01-31 14:44:13)
- 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歷史、現實與法理 (2024-01-21 00:00:47)
- 試析新形勢下深化兩岸文化融合發展的意義、機遇和路徑 (2024-01-08 11:27:26)
- 兩岸高等教育融合發展:目標達成、風險管控與福建實踐 (2024-01-08 11:19:19)
- 對朝鮮半島局勢及韓國政治的一些觀察 (2024-01-08 11:10:30)
- 第十四屆華人學者台灣問題研討會紀要 (2023-12-31 00:16:06)
- 美國國會加強涉華負面立法:意圖、影響及前景 (2023-07-03 10:4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