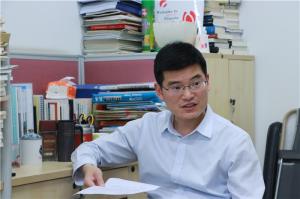|
| 鐘飛騰(中評社 劉柯岑攝) |
至於可借鑒的方面,美日當年解決貿易摩擦的辦法是將雙邊的貿易摩擦轉變為多邊談判的一部分,就是把GATT轉變為WTO。日美把雙邊的貿易赤字、貿易失衡問題轉變成一個多邊的內容。轉變的方式是,日本通過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投資,以此帶動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然後通過發展中國家向美國出口。這樣的調整使得美國所統計出的貿易赤字來源呈現出分散的狀態,也就降低了美國對貿易赤字問題的敏感性。
如今,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也可以通過多邊體制和規則的調整來解決。中國自己實際上也開始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了。中國通過“一帶一路”、通過國際產能合作等,把一部分產能轉到相關的國家,比如說把我們的一些紡織品轉到東南亞地區的越南、柬埔寨以及南亞地區的孟加拉國等,甚至也可以轉移到非洲,這些國家對美國的出口至少在統計上來講就不算是中美之間的貿易,儘管這些國家的紡織業的發展也需要中國公司的支持。把“雙邊”變成“多邊”是美日解決貿易摩擦的經驗中最重要的一條,而且現在比30年前有著更加有利的條件。20世紀80年代以後,世界經濟結構發生變化,跨國公司日漸主導全球貿易,使貿易在國家之間的轉移變得更為容易。另外一種思路是,我們提出了第三方市場合作,即“中國+發達國家+發展中東道國”這樣一種新的機制性安排,除美國之外的很多發達國家對這一思路都是贊同的。因為對很多發達國家來說,在面臨世界經濟前景高度不確定時,中國這樣巨大規模、處於高速成長中的市場是一種穩定器,通過聯手中國去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將獲得更高的回報率。
制度也是調整利益紛爭的一種容器或者一種設計。我們可以去達成一個新的多邊制度框架,然後就能夠把利益衝突約束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範疇。就此而言,無論是WTO,還是其他類型的機制,都需要一種新的思路。比如,我們可以與美國討論是否把“一帶一路”發展成一個新的多邊國際組織。但是也要看到,中美之間的衝突實際上不僅僅是利益衝突,中美衝突可能涉及到戰略、霸權、文明,協調起來的時間成本也是巨大的,因此不能過高期待中美之間短期內解決摩擦的前景。
中評社:日本作為中國“周邊外交”與“大國外交”的交匯點,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過程中的重要影響因素。日本對待“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經歷了從抵制、觀望到積極參與的重大轉變,您如何看待日本態度的轉變?
鐘飛騰:日本對“一帶一路”態度的轉變應該說從前兩年就開始了。評價日本對待“一帶一路”態度的轉變,有幾個大的因素需要考慮。第一個因素是經濟層面的。在2012年釣魚島購島危機之前,實際上日本對中國依賴的上升速度已經很快,但是釣魚島危機爆發之後,這種依賴速度又下降了。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特朗普表達了很多關於貿易保護主義的觀點,這對日本的影響非常大,導致日本的外貿方向發生轉變,中國又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傳統上,經濟財團在日本的影響是很大的。日本政府受到了國內經濟團體的壓力,導致其要慎重對待中國的作用。因為客觀上來講,日本國內與中國的經濟聯繫在加深,這種聯繫將進一步隨著中國的發展而強化,但在政治安全上日本的保守勢力又跟美國保持著緊密聯繫,對中國的發展有很大的擔憂,因而並不希望日本在經濟上過分靠攏中國,但這種態度對日本在中國經營的公司和投資是很不利的。所以,日本政府對華政策變化是有經濟社會基礎的。
第二個因素是特朗普正式當選以後諸多非常眼花繚亂的動作,打擊了國際社會對多邊貿易體制的信心。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的口號,什麼事都要先算賬,而且是算經濟賬。特朗普要將原來美國歷任總統所做的承諾和制度安排重新來過,他是一個一切都要推倒重來的總統,他同歷屆二戰以後我們所熟悉的美國總統風格範式都是不一樣的。而二戰以後的日本基本上是在美國的庇護下成長起來的,儘管20世紀80年代發生了嚴重的貿易摩擦,但是美日之間的基本框架沒有變化,傳統美日關係的基石之一是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這個秩序在冷戰結束後得到進一步強化,甚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也沒有使他崩潰。但是,美國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為卻是要放棄這個基石,做一番前所未有的調整,使之符合美國中下層的利益。就近期而言,這個衝擊遠比中國崛起帶來的影響大。特朗普總統上任以的施政風格和理念,對日本的衝擊非常大,甚至可以說是致命的,日本政府要進行大範圍的政策調整也是勢所必然。
第三個因素是同中國雙邊意義上的。即使沒有前面兩個因素,對於日本來講,在審視亞洲和中國的崛起過程當中,它也要跟隨潮流。因為中國崛起的一個大的環境背景就是亞洲的崛起。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經濟先開始起飛,然後七八十年代亞洲“四小龍”開始崛起,接下來是中國、印度。亞洲是一個很大的體量,如果按照PPP購買力平價算,實際上亞洲已經超過七國集團總量。如此大的一個體量,對於日本來講,它肯它要將其戰略和外交重心往這邊轉移。如果說日本對外戰略有一個基軸的話,那麼這個軸心的基本特點是強大的一方,隨著世界經濟增長重心前所未有的往亞洲轉移,日本對外戰略遲早要反映出這一趨勢。
日本要往亞洲這邊轉移,在這個過程當中必須要處理好跟中國的關係。日本認識到,只有參與到亞洲的事業當中來,它才能夠與中國一起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維持亞洲的穩定和發展。如果它離開,作為一個離岸平衡觀察者,不參與中國的事,怎麼能夠了解中國的態度?怎麼能夠影響中國的態度?所以日本的姿態就是“參與”,然後在參與過程當中給中國很好的建議,幫助中國來應對當前所謂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種種挑戰。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日本的態度到底有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轉變。如安倍所言,中日關係已經從一種競爭關係轉向了合作,或者全面合作。但我覺得中日兩國之間的分歧還有很多的,中方也要看到這個分歧。比如兩國在東海問題上、釣魚島問題上的分歧。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上,日本還有很大的保留意見。但是總體上我認為,形勢比人強,大勢不可違。中日還是要坐下來合作。中日當前合作的最大亮點實際上就是第三方市場。日本政府如今還是不太願意過多地提“一帶一路”,一方面是因為對美國的一個顧慮,因為日本總歸還是美國的盟友,與美國各界的聯繫非常多、非常頻繁,在表態時多少會受到中美關係狀態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因為擔心提了之後似乎是變成了中國的附庸,在中國未變成世界最強經濟體之前,日本人總體上不會明朗地公開認可中國,這是由日本特殊的文化結構、文化心理導致的。
|